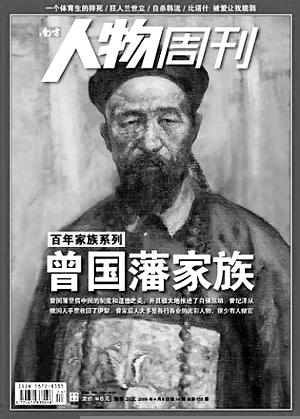| 钟叔河 |
| 刘琨亚 |
| ||
| ||
近两年,《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念楼学短”系列与读者见面……一本本作品,让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中无比耀眼的“钟叔河”这三个字,时隔20年后重新被人们从记忆中捡起。本期专题“钟叔河”,愿如钟先生本人,扼要简明,清风两袖,于平易质朴中凸显风华个性。
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钟叔河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 本报记者 刘琨亚
接近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采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情。但钟叔河还是表现了出异乎于他年龄的精力。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的时候,他的谈兴一直很高,说话语气清晰,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把他的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
在这两年的出版界,可能没有哪一个人比钟叔河风头更劲——虽然他已经离休在家多年。由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今年初,他的“念楼学短”系列出版,让人们对钟叔河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出版家”这个头衔。
钱鍾书、杨绛为他写序
采访很自然的从“念楼学短”开始,钟叔河说,这5本一套的“念楼学短”系列包含了当年出版过的《学其短》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在报社上发表的专栏。其实,这些文章是当年钟叔河为了给孙辈学古文而撰写的。他挑选了一些古文原文,加上自己的翻译和感想。“我所选的这些文章尽量不超过100字,5本书里面,只有两篇文章超过了100字。”他说,当时《新闻出版报》的编辑看到他写的这些东西,让他发表出来。钟叔河之所以愿意把这些文字拿去发表,并不是为了稿费,而是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稿子很难保存,“成了铅字就有了存稿”。
最让钟叔河高兴的是,杨绛先生专门为“念楼学短”系列撰写了序言,当年他的“走向世界丛书”正是钱锺书写的序。为此,杨绛先生还专门给钟叔河的信中说道,这是钱锺书第一次主动为人作序。“对于我来说,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我的前辈,他们能够为我作序,让我很感激,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谈到”念楼学短“的文字,钟叔河显得颇为自信,他说,自己并没有采取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直译的方式,在他看来,古今的直译是很难表现原文的意思。“过去和现在的语境已经不同了,中国的语言不断变化,名词、动词、语法都不同,意译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意境。”他告诉记者,“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运动是一种进步,但文言文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程式化。“文言文而且非常简练,而且自从文言文出现以后,一直到明清以前的人,都能够看得懂。白话的发展变化很快,还有很多方言,时间久远有些意思就不好理解。元朝的诏书就全部用蒙古语的白话写成,到现在是最难弄懂的文献。”
“我不是语文教员出身,也不想教别人什么,写这些东西的初衷是给外孙女学习,后来是借古代的文章来发一些现代的感想。”钟叔河说,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去读,应该会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就怕现在没有人愿意这么费事地去读书了,那就是我最大的悲哀。”看得出,这才是钟叔河最担心的,他特别引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句古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最想做的两件事都已经做了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一件是编一套《周作人全集》。“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已经做了,虽然还没有做完,但我觉得对自己也有交代了。”这位80岁的老人自豪地说。
钟叔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他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走向世界丛书》是他编辑的第一套图书,这套书也为他奠定出版界的地位。
钟叔河告诉记者,平反以后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报社而是到出版社,是因为出版界的自由度比报社大一些,能够出一些自己想要出的书。”
《走向世界丛书》的想法是受到狱友朱正的启发。当时,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探研国家、文明兴亡的规律。两人认为,“文革”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使得一些普世价值被人们抛弃了。“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这种传统使得国家很有凝聚力,但长期大一统的格局也让我们固步自封,呈现出一种保守性——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外向的民族。”
(下转A14版)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到了清政府灭亡的1911年,实际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球文明的时期,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不同地区文明的划分。1840年开始,就有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记录了在西方社会的见闻,也记录了自己对西方的看法,我就是把这些见闻和看法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这些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根据这种判断,钟叔河很快设定了框架: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从1840年到1911年。
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事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更何况,钟叔河还为每本书都写了序论,长的三万多字一篇,少的也有一万多字。他后来的两部著作《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和《从东方到西方》,正是在这几十篇序论的基础上写成。
丛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轰动,钱锺书、萧乾、陈原等人纷纷来信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发表了书评,誉为“一套学习近代史的好丛书”。后来,钱锺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序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
谈到丛书的重印,钟叔河说,从这些先哲们的书中就能够看出,学习洋务不仅仅是学习制造枪炮使用机器,更要学文化学观念。“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还在继续,所以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仍然存在。”
最想做的是写自传总结自己
而编辑“周作人全集”的心愿,这源于他和周作人的一段书信交往。当时,钟叔河被下放到街道拉板车做劳力,那段时间,他看了大量的书籍,他看《希腊的神与英雄》时,对其中很多名字都不认识,他联系出版社,想和作者取得联系。“那时候出版社编辑非常负责任,把我的信转给了作者。”收到回信,钟叔河才知道这个署名“周遐寿”的作者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告诉钟叔河,人名都是通过希腊的原音翻译过来的,他认为这样比通过英文音翻译过来更严谨。
从那以后,钟叔河开始和周作人开始了书信往来,“我没有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在劳动,没有很多的时间和财力购书,他就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有一种感激之情。”对周作人了解越多,他就越想出周作人的全集。出版周作人全集,同样面临风险,不过,钟叔河却巧妙地拿到了有关人士鼓励他出好周作人文集的信,他笑言自己很狡猾,先拿了“尚方宝剑”。后来,他出版了各类周作人的作品,直到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算是完成了他的这个心愿。
《走向世界丛书》最终只出了36种,是很多人都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钟叔河自己反而不这样看。虽然他把100本的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钟叔河说,他现在没有精力再继续编这套书,“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最好有出版社找到负责任,真的能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来完成这套丛书。”他表示,如果没有人做,他会考虑把书卖掉,毕竟当时都是自己花钱收回来的。
他现在不编书、不写小文,他最想做的事情, 写一本自传,为自己做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