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海光(1919~1969)
 |
殷海光(1919~1969) |
 给思想消色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思想知识化,将知识科学化,再将科学量化、数学化、逻辑化的过程,其论说方式不仅误解了思想,也误解了科学。误解思想,是以知识衡准思想,将思想混同于“理性”,取消思想的独立价值与主体特征;误解科学,是将科学片面化、物化,无视科学进程中的主体介入、范式生成与文化传承。 在殷海光看来,知识的有效性只在其客观性,但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注意到,即使对于经验科学事实而言,知识也无法摆脱主体认知的作用。知识的效准,与其说是在纯理推论、在逻辑推演中,不如说是主体间的一种约定,是科学统一体内部互动的结果。在科学知识体系内,人的认知、人的主体性、主体间的交流与认同,不仅无法抹杀,而且地位重要。这正是波普等科学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使用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这一术语的背景。 但殷海光的知识观与科学观中没有“主体”/“主观”(subjective)之类的地位,更不会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这样的术语。主体被禁闭,“主体间”自然不可能存在。这一禁闭导致主体的干枯,也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熟视无睹。科学成为纯知纯理的世界,成为排除了科学研究者主体地位的自主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封闭的、物化的,也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殷海光既然为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人,这里不妨引用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段话作为注解。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曾经说: 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务、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看法。 伯林还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道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7页)。以为未经批判、未经逻辑检验、不合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有颜色的思想”,必须消色乃至清除,这其实是取消思想,是将复杂的世界平铺而物化、量化;将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文世界)单面化、抽象化、物化。这种“普遍效准”的追求,其实是取消文化、道德。 这就是殷海光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强行译作“客观知识”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在道德重构、文化重建问题上深感无力、甚至绝望的根源。 二 一般认为,殷海光的困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思潮造成的,此说不假,却不尽如斯。其实,就殷海光的学思进路来看,其精神气质更多的是在“后五四”氛围中养成的,要解释“后五四”,非长篇巨制不能尽言,这里只好避重就轻,仅以一个人物来呈现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变形与断裂。 终其一生,殷海光始终认定自己是“五四后人物”。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真正的五四人物牟宗三,终其一生不将自己归入五四中人,对五四话题多有回避。更有趣的是,殷海光始终要给思想褪色,而牟宗三却以弘扬“有颜色的思想”为己任。拿五四中人牟宗三的科学知识观与殷海光对比,不仅可以凸现五四与“后五四”精神之别,展现“后五四”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抽象与意识形态化,更可以呈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困境之肇源。 但这里只能紧扣科学知识话题。 牟宗三长殷海光10岁,其学思进路,与殷海光颇有一致之处,求学阶段正在五四时期,入学门径也是逻辑学、哲学。 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其实是以梁启超一系的人物为中心,周边人物包括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林宰平、金岳霖、丁文江、张荫麟等等。五四时期的“中西文明”之争、“西方文明分化”之争、“科玄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等等,都是这个圈子内部话题引发的。如果思想的原创力指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一系人物无疑是真正的提问者,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头脑与灵魂。从此后独立体系创设角度看,基本上也只有他们的成就泽被后世、历久弥新。五四的思想世界就是以他们的话题为中心,搅进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新锐,而激出此后的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分天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三分局面是基本格局。但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五四的话语中,“三分天下”成了左右对抗,五四思想的三足鼎立被简化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二分格局,并被意识形态化了。 从精神气质角度讲,牟宗三所受的熏陶,正是被“后五四”遮蔽并边缘化了的梁启超系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知识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是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意识的高扬。正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突破了胡适一派浅薄的理性主义与陈独秀一派浅薄的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思想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乃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但这些,却在“后五四”的意识形态化中,抽空成“科学、民主”这两个口号。 牟宗三涵泳其中的五四,是那种原生态的五四,是还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是“科学”还没有沦为“科学主义”的五四。这在牟宗三对怀特海思想的欣赏与批判中可见一斑。 牟宗三说,怀特海的宇宙论是数学的、美感的,但其美感与直觉却是外在的,“所以他是泛客观主义,泛宇宙论的铺排”。“生命一词,在他的系统中,并不占有地位。他并不能正视生命,就生命之如其为生命,生命归其自己,恰当地就之以言道德与宗教。他把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自然之流转’。转化成缘起事之过程。他虽亦讲创造,亦讲动力,亦讲潜能,但都亦转成外在的、物理的、泛宇宙论的,至多是亚里士多德型的,而不是生命的,精神的生活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1页)。 牟宗三认为,怀特海“极不喜这太有颜色的心灵。这凸出的认知主体。而极力想往下拖,以泛宇宙论的客观名词、无色的名词,描述之。这就是外在化了。他把生命外在化,把认知主体外在化,至于道德、宗教的心灵主体,则根本未接触得上。因此,他系统中的上帝,亦只是数学与物理的美感与直觉下泛宇宙论系统中的上帝,不是生命中的上帝,道德宗教中的上帝”(《五十自述》,第51页)。 不讲主体,不能正视生命,缺乏历史意识与道德宗教情感,是不能讲文化的。也就是在这点上,牟宗三感觉到怀海特的不足,而转向此后新儒家思想的开创,转向“有颜色思想”的创造。 显然,殷海光的五四,已经不是牟宗三的五四。五四传统被独占、分割,五四精神也因此扭曲而干枯。殷海光精神涵育期,正是处在这种“后五四”的影响下,这是与民族的悲剧相始终的个人心智的悲剧。但问题不仅如此,在殷海光的学思进路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专业训练,与30年代自由主义生存处境之逼仄,更是影响深远的两个层面。 由于这些少有人注意,故这里对殷海光学思涵育期,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略作梳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期,当时的哲学领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天下,这仅从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乃纯思,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哲学对于实在,只形式地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分析哲学家洪谦更是主张,“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内容,仅是关系的组合,这关系的组合的模写,或者有论理性的符号,句子,或者有文法性的言词句子,问题如:世界舍‘形式模写’的理解外,还有他的最后的实在性否?是无意义的,是不可答复的”(《哲学评论》第7卷第3期)。 哲学界的玄思确实过于高蹈了,但这样的哲思毕竟是当时思想界的底蕴。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不愿在这样的玄谈中凌空蹈虚,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左右势力接火对阵。 左的,如共产主义、新启蒙运动,大众文化,其色殷红;右的,如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其色青苍。在左支右绌的挤压中,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只能自己去创造,这便有了“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有了不沾染颜色、保持思想清明、纯洁的诉求。朱光潜那时便呼吁,要守住象牙塔的精纯,“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为流俗化;因此思想的任务在拒绝肤浅虚伪时尚、市场偶像。”蒋?华1937年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也呼吁不依傍权威、不趋步时尚,不追求普遍的信仰;梁实秋更是直接批判思想界的左右倾,指出左、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的思想。” 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左、右双重压力,故主张不依傍、不信仰,提倡思想的个体性,提倡思考的独立。因此,思想运动一方面紧随哲学主流,从事实的驳杂中抽身而退,追求形而上的纯思、采用语言分析与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的阵地上建立自己的阵营,防守学术之城,拒绝“色彩污染”。这,正是殷海光学术训练期的时代氛围,也是殷海光师承的基本脉理。 但“思想自由”的口号,曾经被左倾色彩的新启蒙运动抢了过去,自由主义者只好再退一步,将“思想自由”转换为“自由思想”。自由主义者这一步之退,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得寸进尺,积尺成丈,新启蒙运动干脆通吃,因而有了陈伯达“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之口号:“思想自由”外争话语权力,“自由思想”构建防守堡垒。自由主义的阵营,于是全线崩溃,而只好谈谈纯粹学术与逻辑科学了……50年代到台岛之后,殷海光重拾思想批判旗帜,那一段记忆该是宛然在目。旗号当然需要改换,炉灶更需另起,而思想实质不妨一袭其旧,“自由思想”的口号于是变成了“无颜色的思想”命题。 “思想自由”一变为“自由思想”,再变为“无色思想”,“思想自由”所承担的政治批判、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就冰消雪解,“思想”成了思想家们的“家务事”。自由主义在退回内心、退回学术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的思想战场。 三 从殷海光的精神气质看,尽管一直以来他都以弘扬“科学”为己任,但却始终无法从现实关怀中抽身而退。这正是他的个性、他的使命所在,或者,是他注定了的命运。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崇尚逻辑的思想人物,在骨子里乃是一个斗士、一个烈士、一个被道德激情捕获,与科学、逻辑之冷峻最为隔膜的人。 殷海光晚年,才意识到这一缺陷,但已无力弥补。反思太晚,而且还来自外缘。这外缘,是他的学生林毓生。 林毓生以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展现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学问深入生命,见功底、见慧思的研究。林毓生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显示您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极度的道德激情)和poetical inspiration(诗性智慧)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证实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因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道德激情的道路。但是,道德激情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紧张、假如不是冲突的话,这种张力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负担”(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林毓生点醒了殷海光,他开始意识到“无色思想”命题的荒谬,人,终究不是逻辑的推演机;政治社会的变动,也并不遵循逻辑与理性;知识也许能给人清明,却无法予自身以力量;尤其是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如何能化约为灰色的理论?在回复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感叹:“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 殷海光开始理解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中断的悲苦,在面对国人浓郁的血缘意识时,他产生了一种准宗教感: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3页) 生命意识的苏醒、文化意识的贯注,殷海光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他一贯提倡的科学知识的反省:连自己这样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人,也深陷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沼,大半辈子追寻“思想的无色”,却最是沾染了浓郁的色彩,思想的清明,难道真的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惊回首”,对于生命将尽的殷海光,确实是太残酷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也来得太晚了些。 在思想问题上,新儒家反倒与革命者更为接近。牟宗三强调思想的颜色,强调主体意识;革命者孙中山也早说过,“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为指南。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力量的一部分,虽期盼作为,但终无所成,不仅因其与现实隔膜,缺乏行动之力,也因为这种思想运思的错误。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对于这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清明或许能满足一己之趣味,却也足以障碍思想的传播、窒息思想的生机。而陈义过高,落地无根,不仅是殷海光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困境。造成这一结局的,又因为自由主义对五四文化的话语改造,将五四精神扭曲、单线化、意识形态化,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空间内,试图独占五四成果,从而窒息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失其淋漓元气,而遗其干瘪躯壳,思想之斑斓转成语言之牢笼,真所谓“种因食果,屡试不爽”!走笔至此,悲从中来。 然而,回首前尘,我们却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至今还迷失在“后五四”的浓雾中,生活在单色光波的逼仄空间。长期的熏染造成的选择性色盲已经侵入我们的文化机体,甚至成为我们的自然生命,仿佛承自祖先遗传。其后果,是生命意识的萎顿、生命尊严的丧失;文化土壤的沙化、文化意识的淡漠;创造能力的萎缩、想象空间的干枯……
给思想消色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思想知识化,将知识科学化,再将科学量化、数学化、逻辑化的过程,其论说方式不仅误解了思想,也误解了科学。误解思想,是以知识衡准思想,将思想混同于“理性”,取消思想的独立价值与主体特征;误解科学,是将科学片面化、物化,无视科学进程中的主体介入、范式生成与文化传承。 在殷海光看来,知识的有效性只在其客观性,但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注意到,即使对于经验科学事实而言,知识也无法摆脱主体认知的作用。知识的效准,与其说是在纯理推论、在逻辑推演中,不如说是主体间的一种约定,是科学统一体内部互动的结果。在科学知识体系内,人的认知、人的主体性、主体间的交流与认同,不仅无法抹杀,而且地位重要。这正是波普等科学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使用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这一术语的背景。 但殷海光的知识观与科学观中没有“主体”/“主观”(subjective)之类的地位,更不会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这样的术语。主体被禁闭,“主体间”自然不可能存在。这一禁闭导致主体的干枯,也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熟视无睹。科学成为纯知纯理的世界,成为排除了科学研究者主体地位的自主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封闭的、物化的,也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殷海光既然为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人,这里不妨引用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段话作为注解。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曾经说: 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务、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看法。 伯林还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道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7页)。以为未经批判、未经逻辑检验、不合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有颜色的思想”,必须消色乃至清除,这其实是取消思想,是将复杂的世界平铺而物化、量化;将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文世界)单面化、抽象化、物化。这种“普遍效准”的追求,其实是取消文化、道德。 这就是殷海光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强行译作“客观知识”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在道德重构、文化重建问题上深感无力、甚至绝望的根源。 二 一般认为,殷海光的困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思潮造成的,此说不假,却不尽如斯。其实,就殷海光的学思进路来看,其精神气质更多的是在“后五四”氛围中养成的,要解释“后五四”,非长篇巨制不能尽言,这里只好避重就轻,仅以一个人物来呈现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变形与断裂。 终其一生,殷海光始终认定自己是“五四后人物”。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真正的五四人物牟宗三,终其一生不将自己归入五四中人,对五四话题多有回避。更有趣的是,殷海光始终要给思想褪色,而牟宗三却以弘扬“有颜色的思想”为己任。拿五四中人牟宗三的科学知识观与殷海光对比,不仅可以凸现五四与“后五四”精神之别,展现“后五四”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抽象与意识形态化,更可以呈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困境之肇源。 但这里只能紧扣科学知识话题。 牟宗三长殷海光10岁,其学思进路,与殷海光颇有一致之处,求学阶段正在五四时期,入学门径也是逻辑学、哲学。 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其实是以梁启超一系的人物为中心,周边人物包括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林宰平、金岳霖、丁文江、张荫麟等等。五四时期的“中西文明”之争、“西方文明分化”之争、“科玄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等等,都是这个圈子内部话题引发的。如果思想的原创力指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一系人物无疑是真正的提问者,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头脑与灵魂。从此后独立体系创设角度看,基本上也只有他们的成就泽被后世、历久弥新。五四的思想世界就是以他们的话题为中心,搅进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新锐,而激出此后的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分天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三分局面是基本格局。但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五四的话语中,“三分天下”成了左右对抗,五四思想的三足鼎立被简化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二分格局,并被意识形态化了。 从精神气质角度讲,牟宗三所受的熏陶,正是被“后五四”遮蔽并边缘化了的梁启超系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知识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是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意识的高扬。正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突破了胡适一派浅薄的理性主义与陈独秀一派浅薄的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思想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乃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但这些,却在“后五四”的意识形态化中,抽空成“科学、民主”这两个口号。 牟宗三涵泳其中的五四,是那种原生态的五四,是还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是“科学”还没有沦为“科学主义”的五四。这在牟宗三对怀特海思想的欣赏与批判中可见一斑。 牟宗三说,怀特海的宇宙论是数学的、美感的,但其美感与直觉却是外在的,“所以他是泛客观主义,泛宇宙论的铺排”。“生命一词,在他的系统中,并不占有地位。他并不能正视生命,就生命之如其为生命,生命归其自己,恰当地就之以言道德与宗教。他把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自然之流转’。转化成缘起事之过程。他虽亦讲创造,亦讲动力,亦讲潜能,但都亦转成外在的、物理的、泛宇宙论的,至多是亚里士多德型的,而不是生命的,精神的生活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1页)。 牟宗三认为,怀特海“极不喜这太有颜色的心灵。这凸出的认知主体。而极力想往下拖,以泛宇宙论的客观名词、无色的名词,描述之。这就是外在化了。他把生命外在化,把认知主体外在化,至于道德、宗教的心灵主体,则根本未接触得上。因此,他系统中的上帝,亦只是数学与物理的美感与直觉下泛宇宙论系统中的上帝,不是生命中的上帝,道德宗教中的上帝”(《五十自述》,第51页)。 不讲主体,不能正视生命,缺乏历史意识与道德宗教情感,是不能讲文化的。也就是在这点上,牟宗三感觉到怀海特的不足,而转向此后新儒家思想的开创,转向“有颜色思想”的创造。 显然,殷海光的五四,已经不是牟宗三的五四。五四传统被独占、分割,五四精神也因此扭曲而干枯。殷海光精神涵育期,正是处在这种“后五四”的影响下,这是与民族的悲剧相始终的个人心智的悲剧。但问题不仅如此,在殷海光的学思进路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专业训练,与30年代自由主义生存处境之逼仄,更是影响深远的两个层面。 由于这些少有人注意,故这里对殷海光学思涵育期,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略作梳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期,当时的哲学领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天下,这仅从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乃纯思,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哲学对于实在,只形式地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分析哲学家洪谦更是主张,“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内容,仅是关系的组合,这关系的组合的模写,或者有论理性的符号,句子,或者有文法性的言词句子,问题如:世界舍‘形式模写’的理解外,还有他的最后的实在性否?是无意义的,是不可答复的”(《哲学评论》第7卷第3期)。 哲学界的玄思确实过于高蹈了,但这样的哲思毕竟是当时思想界的底蕴。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不愿在这样的玄谈中凌空蹈虚,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左右势力接火对阵。 左的,如共产主义、新启蒙运动,大众文化,其色殷红;右的,如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其色青苍。在左支右绌的挤压中,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只能自己去创造,这便有了“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有了不沾染颜色、保持思想清明、纯洁的诉求。朱光潜那时便呼吁,要守住象牙塔的精纯,“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为流俗化;因此思想的任务在拒绝肤浅虚伪时尚、市场偶像。”蒋?华1937年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也呼吁不依傍权威、不趋步时尚,不追求普遍的信仰;梁实秋更是直接批判思想界的左右倾,指出左、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的思想。” 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左、右双重压力,故主张不依傍、不信仰,提倡思想的个体性,提倡思考的独立。因此,思想运动一方面紧随哲学主流,从事实的驳杂中抽身而退,追求形而上的纯思、采用语言分析与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的阵地上建立自己的阵营,防守学术之城,拒绝“色彩污染”。这,正是殷海光学术训练期的时代氛围,也是殷海光师承的基本脉理。 但“思想自由”的口号,曾经被左倾色彩的新启蒙运动抢了过去,自由主义者只好再退一步,将“思想自由”转换为“自由思想”。自由主义者这一步之退,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得寸进尺,积尺成丈,新启蒙运动干脆通吃,因而有了陈伯达“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之口号:“思想自由”外争话语权力,“自由思想”构建防守堡垒。自由主义的阵营,于是全线崩溃,而只好谈谈纯粹学术与逻辑科学了……50年代到台岛之后,殷海光重拾思想批判旗帜,那一段记忆该是宛然在目。旗号当然需要改换,炉灶更需另起,而思想实质不妨一袭其旧,“自由思想”的口号于是变成了“无颜色的思想”命题。 “思想自由”一变为“自由思想”,再变为“无色思想”,“思想自由”所承担的政治批判、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就冰消雪解,“思想”成了思想家们的“家务事”。自由主义在退回内心、退回学术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的思想战场。 三 从殷海光的精神气质看,尽管一直以来他都以弘扬“科学”为己任,但却始终无法从现实关怀中抽身而退。这正是他的个性、他的使命所在,或者,是他注定了的命运。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崇尚逻辑的思想人物,在骨子里乃是一个斗士、一个烈士、一个被道德激情捕获,与科学、逻辑之冷峻最为隔膜的人。 殷海光晚年,才意识到这一缺陷,但已无力弥补。反思太晚,而且还来自外缘。这外缘,是他的学生林毓生。 林毓生以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展现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学问深入生命,见功底、见慧思的研究。林毓生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显示您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极度的道德激情)和poetical inspiration(诗性智慧)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证实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因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道德激情的道路。但是,道德激情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紧张、假如不是冲突的话,这种张力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负担”(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林毓生点醒了殷海光,他开始意识到“无色思想”命题的荒谬,人,终究不是逻辑的推演机;政治社会的变动,也并不遵循逻辑与理性;知识也许能给人清明,却无法予自身以力量;尤其是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如何能化约为灰色的理论?在回复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感叹:“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 殷海光开始理解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中断的悲苦,在面对国人浓郁的血缘意识时,他产生了一种准宗教感: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3页) 生命意识的苏醒、文化意识的贯注,殷海光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他一贯提倡的科学知识的反省:连自己这样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人,也深陷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沼,大半辈子追寻“思想的无色”,却最是沾染了浓郁的色彩,思想的清明,难道真的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惊回首”,对于生命将尽的殷海光,确实是太残酷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也来得太晚了些。 在思想问题上,新儒家反倒与革命者更为接近。牟宗三强调思想的颜色,强调主体意识;革命者孙中山也早说过,“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为指南。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力量的一部分,虽期盼作为,但终无所成,不仅因其与现实隔膜,缺乏行动之力,也因为这种思想运思的错误。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对于这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清明或许能满足一己之趣味,却也足以障碍思想的传播、窒息思想的生机。而陈义过高,落地无根,不仅是殷海光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困境。造成这一结局的,又因为自由主义对五四文化的话语改造,将五四精神扭曲、单线化、意识形态化,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空间内,试图独占五四成果,从而窒息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失其淋漓元气,而遗其干瘪躯壳,思想之斑斓转成语言之牢笼,真所谓“种因食果,屡试不爽”!走笔至此,悲从中来。 然而,回首前尘,我们却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至今还迷失在“后五四”的浓雾中,生活在单色光波的逼仄空间。长期的熏染造成的选择性色盲已经侵入我们的文化机体,甚至成为我们的自然生命,仿佛承自祖先遗传。其后果,是生命意识的萎顿、生命尊严的丧失;文化土壤的沙化、文化意识的淡漠;创造能力的萎缩、想象空间的干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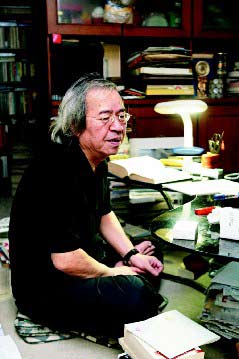 |
| “坐”家,就是这种长年盘腿的书写姿势,让南方朔脚踝骨外侧练出两个大黑痂。 |
 |
| 小学生王杏庆(南方朔),脸上有种不服输的神情。 |
 |
| 寒暑假是南方朔当年打工攒钱黄金期,为大树量身高、胸围,因此走遍台湾大山。 |
 南方朔(后排右二)与母亲、家中五姐妹合影。父亲死后,他是家中唯一男人了。 |
 |
| 南方朔盘坐在阁楼的小茶几前写作,猫咪球球是书僮,连书桌都有它的位置。 |
 龙应台
龙应台| 龙应台:目送 |
|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
| 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
|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09-12-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
 龙应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如果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都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记者 苏枫) |

| 人物:包益民 穷创意是可耻的! | |||
| | |||
包益民,台湾包氏国际公司创办人。曾任威顿与肯尼迪公司创意执行、智威汤逊公司创意总监、李奥贝纳公司创意总监。曾获Communication Arts Design Annual、时报广告金奖等近50项奖项。2001年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我当初也考虑过做免费杂志,但那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在哪里?任何东西,只要是送的就不会被珍惜。 检测某个品牌好坏与否,有个方法:看别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 从开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想找些没钱的客户——从穷客户那里是赚不到钱的。 不怀孕的人总是比怀孕的人多。但假如所有怀孕的人,或其中一半的人穿我的衣服,那已经很不错了。小众市场也是可以投资的,关键在于你的影响力。 包益民,男,39岁,胖。有一妻一女。 2005年上半年,台湾年轻族群中流行两个话题:台客,《PPAPER》。前者的讨论反映出台湾年轻人对本土文化及乡土情怀的回归;后者的火爆则同时见证了他们对进军国际创意工业的期许。包益民是《PPAPER》的制造者。而早在《PPAPER》问世之前,包益民已经是台湾的话题人物。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包益民10岁那年到泰国生活过3个月,13岁又跟着父亲到巴拿马住了6年。包益民说自己的童年属于“自闭儿童”,不大合群,也不大善于与人交流。随后,包益民到美国读书,先后从罗得岛设计学院和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取得学位。1994年,在取得硕士学位前夕,包益民坐飞机到全美三大广告公司之一的“威顿与肯尼迪”(Wieden & Kennedy,简称W&K)面试,没想到被当场留下,成为当时W&K创作部唯一的亚洲人,负责NIKE的部分电视广告。包益民在W&K工作3年,他说这3年让他真正体验到世界级的好手是怎么做事情的。“W&K最大的优点是永远鼓励你找全世界最好的人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想着找熟人,应该很客观地想世界上谁做这件事最好,你就去找他。”3年后,包益民被李奥贝纳广告公司高薪“挖”回台湾担任创意总监,随后又在另一间4A公司智威汤逊担任创意总监。 1998年9月,感觉在广告公司“走到头”的包益民决心自己创业。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至宜,在一个小公寓里,靠一张餐桌、一台电脑,创立了包氏国际。他们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收费6万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的NU SKIN产品目录。不到5年时间,包氏国际的员工发展到10人,而客户高达500个,业绩2.7亿新台币,业界称2003年其获利保守估计约3成,成为全台湾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之一。包益民在台湾一直话题不断—— 1.包益民收费特别高,在业界数一数二。据说洗发水包装设计费一般也就10万新台币,但包氏定价高达百万。 2.包益民总是与国际级大师合作。他曾带着SKⅡ的产品飞到纽约找著名摄影师Kenji Toma,3张产品照花去150万新台币;2001年,他找加拿大插画家Maurice Vellekoop为作风保守的女鞋AS设计出前卫的插画;2002年说服意大利插画家Jeffrey Fulvimari为“周蕙精选”设计唱片封面;2003,找来全球首位像素创作者Craig Robinson制作陶 《今天没回家》的MTV;2004年邀请迪斯尼卡通大师、三度获得艾美奖的Gary Baseman担任宜兰国际童玩节视觉设计。 3. 2001年,包益民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4.去年,年纪轻轻的包益民以自传形式出了一本书《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封面竟然用的是自己的全裸照。 5.作为一家广告公司,包氏国际从不加班。晚上7点,大家准点下班。7点半给包益民打电话,他已经在家里陪太太和女儿了。 说到包益民的太太胡至宜,那也是个厉害角色。她是台湾著名的文案,不仅写广告,还写散文、出书;是包氏国际的总经理,《PPAPER》的总编辑。但她一点都不像职业妇女,她不喜欢应酬,不喜欢社交,大部分时间她都懒懒散散地,在家喝咖啡,和朋友聊天,只用很少的时间、精力就把工作完成了。包益民说:“我太太属于天才型的,老天给了她很好的天赋,她用最简单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这是她的特色。” 2003年,37岁的胡至宜怀孕。在知道自己怀孕的第一天,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她就跟包益民说:“我不上班了。”胡至宜全心全意在家待产,却发现买不到心仪的孕妇装,她说市面上的孕妇装又贵又难看,久而久之会让女性会失去警戒及羞耻心,任凭身材随意发展。在与包益民商量后,胡至宜决定进军孕妇装市场。成衣市场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包氏国际无法拿出大笔资金,于是胡至宜从以100万新台币起家,创建ive&sean品牌。她在家画了20张服装草图,找打版师朋友试做,完成第一批成品。她舍弃传统经营手法,通过网络经销,结果一炮而红。 2004年底,包益民出人意表地与7-Eleven合作,推出平民化设计生活杂志《PPAPER》。这本用骑马钉装订的80页月刊杂志,每期由8个人用大概10天时间完成,定价49新台币,其价值在台湾市场相当于一包口香糖加两杯饮料。《PPAPER》每期介绍一个国际知名创意品牌或设计师,包括美国时尚大师Fabien Baron、日本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荷兰广告界另类天王KESSELSKRAMER等等。《PPAPER》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第一期售出35000多本,破了台湾设计书销售纪录;从第4期起一跃成为超级商场杂志类销售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周刊类的《商业周刊》、《壹周刊》;如今销售量大约是每期8万本;根据商场POS系统所提供的消费者族群数据(结账时店员目测消费者年龄,在收款软件中键入其年龄层以及所购买的商品),青壮年消费者是主要消费群(约占7成),另外竟然有大约6%的消费者是小学生。 由于第一步的成功,包益民正积极筹备将《PPAPER》改作双周刊,并计划年底至明年初分别进军香港、上海,制作当地版。他透露说,内地版的售价目前预定10元。大有火拼本土杂志的势头。 | |||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